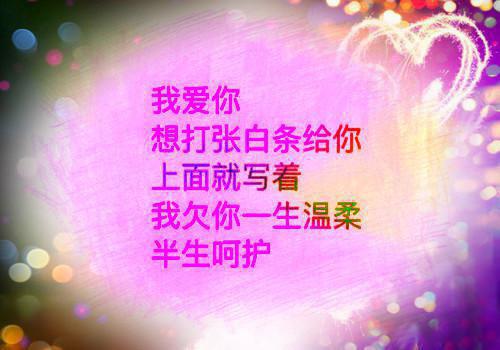亲戚让我偷骨髓给她治白血病全文免费阅读_亲戚让我偷骨髓给她治白血病最新章节
|
1 报志愿时,我妈逼着我学医。 毕业后,我在牙科上班,她却逢人就说看病找我。 后来,舅舅让我给患白血病的舅妈开药,还让我从学校给她找匹配的骨髓。
我说做不到。 可舅妈病死那天,她儿子提着刀冲到我面前,说我害死了他妈。 混乱中,我被连捅几刀。 表哥嫌弃地碾压我的伤口:“不会治病,拿什么钱。” 我失血过多而死。 死后,我才明白他们为何这么怨恨我。 我妈以我学医能看病为由,收取高额礼金。 就为了我舅给的二十万,她竟是连公道都不为我讨回。 再睁眼,我回到舅舅带着舅妈,来找我看病这天。 我笑道:“舅妈,只要我妈愿意给你捐骨髓,你就能活下去,哦,表哥也行!” 1 “你这报的都是什么不三不四的学校,出来能有工作吗?” 报志愿那天,妈妈看着我的电脑说道。 我叹了口气,身体和精神都很是疲惫。 我高考超常发挥,能上一个双一流大学的名牌专业。 爸妈都没文化,一辈子没出过农村。 这些事情他们不懂,我也不怪他们。 为了不耽误自己的分数,我三天没合过眼,四处打听学习怎么报志愿。 最后,我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拟出一份不错的志愿名单来。 可是妈妈却拿锅铲狠狠拍了我的脑袋。 我瞬间感觉眼冒金星,捂着脑袋躲到一边。 妈妈用满是油星的手指重重敲打我的键盘,骂道: “死妮子,你这都是什么学校?计算机,你要给人修电脑啊?我砸锅卖铁供你读书,是叫你给人修东西的?” 我感到无奈,试图解释说: “妈,那不是修电脑的,那是热门专业,能进大厂的...” 我话还没说完,就被妈妈狠狠扇了一个巴掌。 她的力气太大,我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地。 紧接着,她就哭了起来。 “我真是命苦,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砸锅卖铁供你上学。现在好了,你要进厂打工,不如趁年轻找个人嫁了...” 我还想争辩,和她解释说: “不是的妈,你理解错了...” 我的话又一次被她打断,妈妈哭地更加撕心裂: “是,我什么都不懂,我没文化。都赖我行不行,都赖我,我就不该生你下来!” 说着,妈妈开始扇自己耳光。 每一下都清澈又响亮,每一次下手都重得像是要杀人。 她总这样,我都习惯了。 每当我的话不顺着她的意思来,她就会先打我一顿,再哭着抽自己耳光。 我总是顾不上自己的疼痛,先去拦着她自残。 这样的哭闹持续了大概十几分钟,最终以我的妥协作为结局。 妈妈站在我身后,看着我在电脑上输入“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等字样后,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她说: “刘三那个贱人卖药卖死贵,两年在村里建了个新房子,你也学医,挣得多,还能给家里人看病!” 听着她荒谬的发言,我选择了沉默。 没有人能劝动她,这是我十八年来的经验。 我要是敢说她一句不对,她恐怕又要开始扇自己,然后站在楼顶说我要逼死她了吧。 点下提交按钮,我的人生悲剧,也就此拉开序幕。 2 我的成绩够高,考进了外省一所不错的大学学习口腔医学。 比起其他医学专业,这算是轻松的了。 我也知足,在学校里安定下来。 可我没想到,我以为妈妈那句给家里人看病只是句玩笑话。 妈妈却已经向所有亲戚夸下海口,说我在大城市当医生,以后有病来找我就行,我都能看。 一开始,只是一些头疼脑热,摔跤破皮的小事。 就算我不学医,我也能给他们买点感冒药和红花油。 可渐渐的,他们开始问起大病来。 三姨怀了孩子,问我是男是女。 她挺着八个月大的孕肚,站在她男人旁边擦着脑门的汗。 她男人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吃着桌上的花生豆。 他一张嘴,烟味呛的我睁不开眼: “昭儿啊,你给叔看看这是闺女还是小子行不行,叔给好几个大夫买了烟,他们都说是个丫头!” 我心里无语,你都已经塞钱查出来是女孩了,干嘛还来问我。 但我知道三叔脾气爆,所以仔细斟酌着我的语言。 “叔,你跟我姨一表人才的,那生男生女都是人中龙凤!” 他一听我这话,咧着一口黄牙咯咯笑起来。 猛吸了一口烟后吐出几个烟圈,用他精明又恶劣的眼神看着我: “别说这个,你跟叔说,是个儿子吧?” 我有些紧张,吞了吞口水解释说: “叔,我是给人看牙的,不懂妇产科。但是医院的医生也是说法都一样,那大概也没差了...” 啪! 三叔把烟灰缸狠狠咋在桌子上,起身给了三姨一巴掌: “你个赔钱货,天天花我钱还不够,还要再生一个赔钱的贱人霍霍我?” 我起身想去拦,却被三叔一挥手撞到在地,腰还磕到了桌角,我疼的泛起泪花。 三叔拽着三姨的头发,一路拖回了家里。 听着三姨的惨叫,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如果我骗三叔说三姨怀的是儿子,三姨是不是会好过一点。 想到这里,我摇了摇头。 如果骗他,那等三姨生下女儿来,恐怕连我都要一起被打死吧。 我起身揉了揉自己的腰,无意间瞥到被我撞歪的柜子后面居然放着一个纸包。 像是包着不少钱的样子。 可家里穷的很,我连学费都是申请的助学贷款。 哪里会有这么多钱呢。 我伸手想拿起来看看,却在马上碰到纸包的一刻被烫伤了手。 妈妈拿着上一秒还在炒菜的锅铲打向我的手,我的手瞬间起了个巨大的水泡。 我疼的跪在地上尖叫。 “你个白眼狼,还不过来给我做饭!让你娘一个人累死累活伺候你,你也不怕遭天谴!” 无奈,我拿冷水冲了冲伤口后,走进了厨房开始熬粥。 身后,妈妈迅速拿起纸包,藏在了柜子深处。 3 我看着菜板上的鱼和猪肉,就知道今天是弟弟放假的日子。 我在家里,永远只能吃烂菜叶子。 爸妈装都懒得装。 我叫沈昭儿,弟弟叫沈耀祖。 我抹了抹眼泪,用仍然被烫得隐隐作痛地手刮起了鱼鳞。 两个小时后,我把最好的四菜一汤端进了屋里,还把灶台擦了个干干净净。 妈妈已经把弟弟接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把书包扔给我,鞋子也踢到我这里。 他烦躁地瞥了我一眼,转身扑进了妈妈的怀里。 “妈,真是烦死了,老师又拿沈昭儿敲打我!” 他一直这样,从不叫我姐姐。 而是一遍一遍地直呼我的大名,这个祈求他出生的大名。 他和我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只不过比我小两岁。 只不过我是考进去的,他是爸妈交了三万块钱塞进去的。 我总是考年级第一,所以学校里的老师很多都认识我。 也总拿我教育弟弟,他就回来诉苦。 然后,爸妈为了哄他开心,就打我出气。 我给他们盛好饭,然后搬着板凳坐到了屋外,就这昨夜的剩菜吃起来。 比起剩菜,我吃的更多的是眼泪拌饭。 听着他们的欢声笑语,我抬头看着天空。 这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咚! 妈妈拿电视遥控器砸中了我的脑袋,我捂着头回头看,却看见弟弟憋笑的模样。 妈妈喊我,我只好把碗放在地上,转身走进屋内。 “你舅妈身子不舒服,你晚上去看看她。” 我握紧拳头,看着弟弟戏谑恶心的脸,忍不住顶了嘴: “我又不是医生,她不舒服怎么不去医院?” 妈妈闻声,拿起手边的鸡毛掸子向我扑来。 我的身上瞬间泛起了血痕,我想躲,却被弟弟死死摁在原地。 “你个白眼狼,你书都读到哪里去了?都给狗吃了?我让你去你就去,还敢跟我顶嘴?” 一顿毒打后,妈妈和弟弟才坐回沙发上看起了电视。 妈妈咬着后槽牙指着我说: “你今天要是不去,我就把你嫁给后山了王二瞎子,书你也别读了,去给人家生儿子去吧。” 我闭着眼,绝望地点了点头。 还好,暑假就快结束了,等我回学校,就不用再这么受委屈了。 4 傍晚,我提着剁好的两斤肉去了舅妈家。 一进门,就看见舅舅和一群男人光着膀子在院里喝酒。 我一进门,他们都嬉笑着跟我说话。 让我叫他们舅舅,还要拉我的手。 我一阵恶寒,赶紧跑进了屋内,看见床上面如土色的舅妈后又吓了一跳。 “舅妈,您这是怎么了?” 舅妈虚弱地说不出话来,这时,舅舅走了进来。 “白血病,说是要什么碎?你从学校给我们弄点吧,省得花钱哦了。” 白血病?从学校弄点? 他到底下说什么,我的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对舅舅说: “舅舅,白血病可不是小事,得赶紧去医院!还有骨髓捐献,这个是要找人匹配的,不是随便就有的!” 我希望我焦急地语气可以引起他们的重视,可舅舅却满脸不屑。 “去医院得多少钱?你不是医生吗,你给治一下不就行了?” 明明是他家里人的病,可我却比他们急一万倍。 “我怎么可能治的了,还没晚期吧?快送去医院!” “唉行行行,你不能治是吧?你不能治我叫你妈来,你跟她说,我看你能不能治。” 我知道和这个人无法沟通,于是转身去找他的儿子,我的表哥。 “哥,你快送舅妈去医院啊,晚了就来不及了!” “呸,你个贱坯子说什么呢,你咒我妈死?” 争吵间,我妈已经赶来了舅妈家,拧着我的大腿和舅妈一家赔礼道歉。 回去的路上,妈妈一句话也没和我说。 到家后,她只留给我一句话: “滚出我家,我看见你就恶心。没良心的赔钱货。” 那晚,我买了最近的一班车,去车站睡了一晚上后回了学校。 我求了辅导员很久很久,她给我办了留校证明。 终于,我离开了那个人间炼狱。 就算是暂时的也好,我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安宁。 可我才逃离那里不过两个星期,就接到了妈妈的电话轰炸。 舅妈死了,他们让我回去参加葬礼。 放下电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她的病,我真的无能为力。可是如果我能再劝他们两句,让他们把舅妈送去医院呢? 我摇摇头,又起身准备回家。 回去的路上,我下定决心。 吊唁完舅妈我马上就走,不给他们任何伤害我的机会。 可我却怎么也没想到,意外果然比明天先来。 我对着舅妈的遗照磕头,还没来得及起身,就被表哥撞飞了一米远。 他提着刀,狰狞地看着我: “就他妈是你咒我妈死!就是你个贱人给我妈瞎开药,贪了十万还要杀人,看我不弄死你!” 什么? 他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也没机会听懂了。 葬礼上,他连捅我二十刀。 我的鲜血,是葬礼上唯一的颜色。 我的生命,定格在了二十岁那年。 5 我看着地上混乱哄闹的人群,感到阵阵眩晕。 可当我的身体出现在我发眼前,我才终于接受我已经死掉这一事实。 我试着去拍拍妈妈发肩膀,却发现自己已经摸不到任何东西。 我的灵魂,在舅妈的葬礼现场之上漂浮。 我不想去思考什么人死后会去哪里的哲学问题。 现在,我只觉得解脱。 压抑又恐怖的二十年人生里,我没有一天是幸福的。 即便是逃到了离家几百公里的大学,也会在手机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浑身颤抖。 死了也好,死了就不会再害怕了。 活着,还不如死了。 前来吊唁舅妈发宾客目睹了这一场凶杀案,有些害怕地逃离了现场。 有些拿起手机报了警,还象征性的地叫了救护车。 可我这些亲人,甚至我的亲生父母和弟弟,没有一个人在乎我的死活。 他们,在表哥提着刀来到我面前时。 就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我看着自己的尸体觉得不太舒服,寻思着回家去看看他们怎么样了。 我不求他们为我的死痛哭流涕,只求他们不要连我的尸体都置之不管。 好歹给我埋了吧。 回到家中,我却发现他们拿着几个包袱装衣服。 爸爸坐在门口,抽着旱烟。 他手里,数着一沓红色的纸币。 身旁还放着一箱子的钱。 我活了二十年,没见过家里有这么多钱。 妈妈在屋里面收拾着衣服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 弟弟也帮衬着,把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全部放进包袱里。 这是干什么? 我死了,他们难道觉得这个地方晦气,待都待不下去了吗? 想到这里,爸爸起身走进了房间,对妈妈说: “二十万一点不少,算上咱之前那些,能有个三十多万。” 妈妈一听,脸上的笑意完全止不住: “够了!够了,咱们赶紧走,别让那个傻子追过来。” 弟弟扛起包袱,脸上也满是奸笑: “没事,他肯定要坐牢的。沈昭儿也算是解决了个大麻烦,死的值!” 听着他们的交谈,我整个人怔在原地。 突然间,我眼前的景色扭曲起来。 并不像是我正在经历这些事情一样。 而相识一卷录像带,像我播放起我不曾知晓的种种事情来。 像是上天也可怜我死得不明不白,给我开了上帝视角,让我把他们的恶再看得清楚一些。 眼前的一幕幕交易播放着,我的血液似乎都要凝固住了。 看着妈妈收下舅妈的二十万现金后,我连后槽牙都在颤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