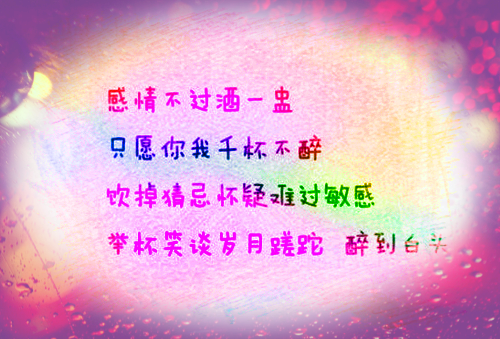全文浏览系统让我攻略反派,她竟住我床底(白凝冰方圆)_系统让我攻略反派,她竟住我床底(白凝冰方圆)全文结局
|
紫藤花串在初夏的风里轻轻摇晃,筛下细碎的光斑,落在我们相扣的十指上。 无名指根部那圈微凉的铂金,带着崭新的、不容忽视的存在感,一直熨帖到心底最深处。 白凝冰依旧单膝跪在那里,仰着脸看我。那双墨玉般的眸子,清晰地映着我傻笑的脸, 里面翻涌的惊涛骇浪——紧张、狂喜、难以置信——在我说出“一直走下去”的瞬间, 骤然凝固,随即如同投入石子的湖面,剧烈地荡漾开一圈圈名为“永恒”的涟漪。
阳光落在她微颤的睫毛上,像栖息着细碎的金粉。她喉结滚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 最终却只是猛地收紧与我交握的手,力道大得几乎要将我的指骨捏碎。她借力站起身, 动作带着一种失而复得般的急切和珍重。下一秒,我整个人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入怀中! 她的手臂如同最坚韧的藤蔓,死死地缠绕着我的腰背, 将我用力地、深深地按进她温热的胸膛里。力道之大,让我几乎喘不过气, 肋骨都发出轻微的**。“唔…班长…轻点…”我闷哼一声, 鼻尖撞在她带着淡淡冷香的衣襟上。那禁锢般的力量瞬间松开了一丝缝隙, 却依旧固执地环抱着我,不肯放离分毫。她的下巴重重地抵在我的发顶, 急促而温热的呼吸喷洒下来,带着一种失语的激动和浓重的鼻音。 “方圆…方圆…”她只是低低地、一遍遍地念着我的名字,声音沙哑得厉害, 像是跋涉了千山万水终于抵达绿洲的旅人,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和巨大的满足。 温热的液体毫无预兆地滴落,浸湿了我头顶的发丝,带着滚烫的温度。她哭了。 那个在所有人眼中无懈可击、冰冷强大的白凝冰,此刻像个迷路许久终于找到家的孩子, 在我怀里无声地落泪。滚烫的泪珠一颗颗砸下,带着灼人的温度, 也带着卸下所有心防后最纯粹的脆弱。【啊啊啊!反派哭了!他哭了! [暴风哭泣]】【呜呜呜…这眼泪值千金!是喜极而泣!是尘埃落定!】【方圆快抱紧他! 他需要你![泪目]】【紫藤花下定终身!妈妈我嗑的CP修成正果了! [疯狂打call]】我的心像是被那滚烫的泪水泡软了,酸酸胀胀的。我伸出手, 更用力地回抱住她微微颤抖的身体,脸颊在她带着湿意的颈窝蹭了蹭, 像安抚一只受惊的大型犬。“嗯,我在呢。”我的声音放得很轻,带着全然的安抚, “班长,不哭了,戒指都戴上了,跑不掉的。”她似乎被我笨拙的安慰逗笑了, 发出一声压抑的、带着浓重鼻音的短促气音,随即把我搂得更紧, 仿佛要将我彻底揉进她的骨血里,永不分离。紫藤花的香气在暖风中静静流淌, 将这一刻的悸动、泪水与誓言,温柔地封存。毕业的喧嚣如同潮水般退去。 白凝冰没有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拉着我,直奔市民政局。填表,拍照, 宣誓……流程快得像按了加速键。当那两本印着烫金国徽的红色小册子递到我们手中时, 我还有些恍惚。照片上,我笑得有点傻气,眼睛亮晶晶的;而白凝冰, 虽然唇角只是微微上扬了一个极小的弧度,但那双注视着镜头的墨眸里, 却盛满了几乎要溢出来的、沉甸甸的光。“恭喜二位,新婚快乐! ”工作人员微笑着递上小本子。“谢谢。”白凝冰接过证书, 指尖在光滑的封面上轻轻摩挲了一下,随即极其自然地将其中一本塞进我的掌心, 另一本则珍重地收进了她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最里层的夹袋里, 动作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占有欲。走出民政局的大门,夏日的阳光有些晃眼。 白凝冰没有松开我的手,反而握得更紧。她侧过头看我,阳光下, 她无名指上那枚与我同款的戒指折射出细碎的光芒。“回家。 ”她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清冷,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尘埃落定般的沉稳和暖意。 我以为她口中的“家”,是我们大学附近那套被她布置得越来越温馨的公寓。然而, 车子却平稳地驶向了市郊,最终停在了一处我从未踏足过的、守卫森严的庄园式别墅前。 巨大的雕花铁门无声滑开,车子驶入,穿过精心修剪的园林, 最终停在一栋极具现代设计感、如同艺术馆般的建筑前。 “这里是……”我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这栋低调奢华的建筑。“我们的家。 ”白凝冰牵着我下车,语气平淡,仿佛在陈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事实,“以后就住这里。 ”【反派の婚房:从黄金鸟笼升级为艺术宫殿![震惊]】【方圆:谢邀,人在庄园, 刚下婚车。[懵圈]】【这房子…得值多少个亿?[瑟瑟发抖]】走进大门, 是挑高近十米的巨大客厅,整面落地窗外是波光粼粼的私人湖景。 室内设计是极致的简约与奢华并存,线条冷硬,色调以黑白灰为主, 处处透着一种不近人情的冰冷感,像一座精心打造的堡垒,也像白凝冰过去内心的写照。 “可能有点冷,”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不适,握着我的手紧了紧,声音放软了些, “以后你按喜欢的布置。”她顿了顿,补充道,“想怎么改都行。”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笔挺西装、戴着金丝眼镜、气质干练的中年男人快步迎了上来, 手里捧着一摞厚厚的文件。“白总,您吩咐的文件都准备好了。”男人恭敬地递上文件, 目光在我身上飞快地扫过,带着职业性的探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白凝冰接过文件, 没有看那男人,而是拉着我走到客厅中央那张巨大的、光可鉴人的黑色大理石茶几前。“坐。 ”她示意我坐下,然后将那厚厚一摞文件推到我面前。“这是什么? ”我看着封面上那些复杂的金融术语和法律条文,一头雾水。白凝冰在我身边坐下, 身体微微向我倾斜,带来熟悉的清冽气息。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翻开文件的第一页, 指向上面一串长得令人眼晕的数字和后面跟着的一长串零。 “这是白氏集团的核心股权**协议,”她的声音平静无波,像是在讲解一道物理公式, “我名下持有的51%原始股,全部无条件**给你。”我:“!!!”大脑瞬间宕机。 白氏集团?那个横跨科技、地产、金融多个领域的庞然大物?51%?!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瞬间拥有了对这个商业帝国绝对的控制权!“班长!你……”我惊得差点跳起来, 舌头都打了结,“这…这不行!这太……”“还有这些,”她仿佛没听到我的惊呼, 修长的手指平静地翻过一页,指向另一份文件, “这是我在瑞士、开曼群岛、以及国内几处信托基金的受益权变更文件, 受益人全部变更为你。”再翻一页,“这是全球七处不动产的所有权**文件, 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庄园,以及纽约、伦敦、东京的几处顶层公寓和私人岛屿。 ”她翻页的速度不快,但每一页掀开,都像在我面前打开了一座金山。文件一份份摊开, 涵盖了她名下几乎所有的动产、不动产、股权、基金、专利、版权……数额之巨,种类之繁, 远超我的想象。“最后这份,”她拿起最后一份装订精美的文件,推到我的面前, 指尖在那份文件的标题上轻轻点了点,“是我个人的遗嘱公证。如果我发生任何意外, 我名下所有剩余财产及权益,包括白氏集团未来的所有收益,全部由你继承。”她抬起眼, 那双墨玉般的眸子定定地看着我,里面没有炫耀,没有施舍, 只有一片沉静的、如同交付生命般的郑重。“现在, ”她拿起一支早已准备好的、镶嵌着碎钻的签字笔,拔开笔帽, 塞进我因为震惊而微微颤抖的手里,声音低沉而清晰, 带着一种斩断所有退路的决绝:“签了它们。”【!!!千亿财产!是千亿财产!】【**! 反派玩真的!全部身家都给了方圆![瞳孔地震]】【这哪是结婚?这是把命都交出去了! [颤抖]】【方圆:人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 [懵圈]】巨大的冲击让我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 我看着眼前这堆代表着天文数字财富的文件,又看看身边这个眼神平静却暗藏惊涛的女人。 她不是在开玩笑,她是认真的。她把她拥有的一切,她奋斗的一切, 她赖以生存和掌控一切的根基,毫无保留地、彻底地捧到了我的面前。这不是馈赠。 这是献祭。“为什么?”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 “班长…白凝冰…你…为什么要把这些都给我?”白凝冰没有立刻回答。她只是伸出手, 指尖带着微凉的温度,轻轻抚上我无名指上那枚崭新的戒指。她的目光顺着戒指,缓缓上移, 最终定格在我的眼睛深处。“因为你说,”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千钧之力, 每一个字都清晰地敲打在我的心上,“愿意收下我的全部。”她的指尖微微用力, 摩挲着戒指冰凉的金属表面,眼神专注而深邃,像是要透过我的眼睛,看进我的灵魂深处。 “我的过去,充满算计和冰冷,不值得留恋。我的未来,或许依旧会有风雨,但只要有你, 就是光明。”她停顿了一下,长长的睫毛垂下,遮住了眼底翻涌的情绪, 声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脆弱和孤注一掷的坦诚:“唯有现在, 我拥有的这一切——财富、地位、权势——它们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她抬起眼,那双墨玉般的眸子里清晰地映着我震惊而心疼的脸, 盛满了最深沉、也最笨拙的赤诚:“方圆,这些,就是我全部的‘现在’。”“我把它给你。 ”她的指尖离开戒指,轻轻捧起我的脸,动作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珍重,目光灼灼, 如同燃烧的星辰:“连同我这个人,我的灵魂,我的全部不堪和……全部的爱。”“都给你。 ”“求你……”她的声音终于带上了一丝难以抑制的颤抖和恳求, 那层坚固的冰壳彻底碎裂,露出内里最柔软也最脆弱的部分。她将额头轻轻抵上我的额头, 温热的呼吸交融,声音低哑,带着浓重的鼻音和深不见底的后怕:“别再……离开我。 ”【‘求你,别再离开我’——暴击![泪崩]】【反派掏心掏肺!把命和钱都给了方圆! [暴风哭泣]】【方圆快签!快抱抱他!他需要安全感! [急死了]】【这该死的、沉重的、毫无保留的爱! [心碎又感动]】巨大的酸涩瞬间冲垮了所有的震惊和迟疑,如同汹涌的潮水, 瞬间淹没了我的心脏,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她不是用财富来炫耀或捆绑, 她是用她所能给予的最沉重的砝码,来填补她内心那深不见底的安全感黑洞, 来换取一个“永不离开”的承诺。看着她眼中那浓得化不开的脆弱和近乎卑微的恳求, 看着她捧到我面前的、如同她生命般沉重的“现在”,我所有拒绝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心疼。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眼底翻涌的热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