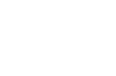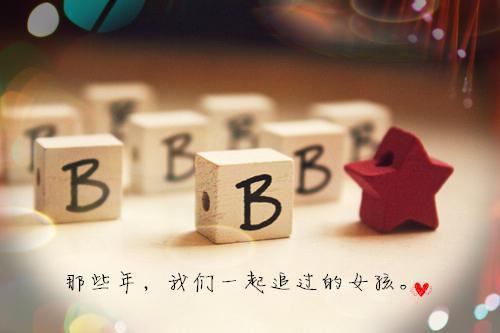东晋风流全文免费阅读_东晋风流最新章节
|
自序 我的新历史小说与性情化写作。 中国历史小说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历史小说”阶段,以罗贯中作品为代表。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只是“帝王小说”,而非真正的“历史小说”,因为它并未洞察历史。当然,《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巨大的。 在写作态度上我提倡“性情化写作”。做人要做性情中人,写作要写性情之作,我一向这样要求自己。性情中人写性情之作,岂不美乎!必大补宇宙元气。中国的“性情传统”应在新世纪大放异彩。
所谓“性情化写作”很简单,那就是本着性情写作,一切由着自己的心。“性情”二字极珍贵,它是情中性,又为性中情,情性和合,人欲尽得;性情双修,大道悠悠,不可以轻言之。 在写作时,如果我们性情不畅,那么写作必不能成。只有在灵气畅通、性情畅快时,我们的写作才可能实现并尽可能出彩。写作其实就是一次心性的投放过程,它的完成程度与创造程度完全取决于我们性情的流露。无性情则无作品。我的“有情工具、无情写作”理论,是说作为写作工具的作者他必须是有情的,而写作本身因为受控于太虚与幻境中人(书中人),它是“绝对理性”的(指受某种指令进行程序化操作),因此是冷冰冰的,无情的。但正因为写作是“无情”的,写作者才特别“有情”。他意识到自己的全部意义在于作为工具本身……人是人性的试验品,作家是写作的工具,那么他一旦不再悲怆于自己仅仅作为工具而非事件起源或终极目的,将会更加豁达地热爱自己的工具身份。他更加有情,他的性情超乎人性之上。他物化,他是大我,他有大爱,他追求大美。性情化写作使他的文思与人性无限放大,其作品吞吐宇宙,出入大荒,能量无尽释放。杜甫诗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言世界之有限,而性情之畅可使天出九重,人出三界,心智合一,永享思维之灵境。佛家言“智海”、“性天”,吾言皆从“情”出。 提倡“性情化写作”的同时我提倡“精细化写作”,很简单:那就是多写、多改,精雕细琢。任何一部大气的作品必有其精细的一面作为支撑,这就像本书中的祖逖既为粗犷的豪士亦为情感丰富的男人一样。 精耕细作的土地更适合作物生长,精雕细琢的写作会丰收更多的思维果实。 这种精细化写作的态度实来源于我们对写作的热爱,对文学的热爱,对语言的热爱。我现在除了留意学习各种文学语言、学术语言外,还特别注重观察各种口语,学习各种非文学语言,如日常生活中的便条、留言条;新闻;商业广告;法律条文;行政文件等等,细看细想都非常有意思,各有文体之妙,各尽文思之奇,皆可兼容并包转化而入我笔下。文学语言只不过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罢了,真正的语言大师要精细到留意自己的临终遗言如何表达。请记住:通过精细化地思考与写作,没有什么意思不可以表达。古人云:“言尽意”,真我师也。郁达夫极其推崇日记与书信这两种文体,现在我更感动于火车站里留言板上的短句,更留意于街头电线杆上贴的寻人启事或租房启事,它们也许蕴藏更多东西,更富有性情。文体必须解放,写作必须开阔。而在众体皆备、众妙将成的状态下,我们的性情化写作必须进行精细化表达!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不满足于“一生只写一部书”的落后想法,出手即成经典,随意莫非大师,而其基础无它:多想、多写、多改。爱写作,永远写作。 要像热爱爱情一样爱写作,要像永远追求神女一样永远追求写作的至高、至美境界。 人是人性的试验品,我们也要一试文学在我们身上究竟能到何等地步! 生活是转瞬即逝的,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唯有“写作”永恒。他应该爱写作更甚于爱生活(其实有时生活可以不爱)。生活是写作的附庸,写作是生活的灵魂。我现在就真切地感觉到我的生活中最能把握的是写作,其外一切总给我飘缈感。虽然虚无让我亲切,但我并不喜欢虚妄的东西。我还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 传统的写作一般指向两处:一是作者内心,二是读者的精神世界。换言之也就是传统的写作或者是写给作者自己看,或者是写给读者看。而如今我感觉我的写作已经在指向上(即“为谁写作”上)走得更远了,那就是:我既不为我自己写作,也不为读者写作,我为书中人写作。这种写作指向的巨大变异无疑是对传统写作的反叛。 是的,我为书中人写作(或云为虚拟世界写作),他们的虚拟构成了我的真实。在写的时候,他们在凝视着我的笔尖。我的稿纸(或我的书页)就是我的屏幕,它由我的笔尖与目光链接了两个真实的虚拟世界。如果我不是为书中人写作我就无法写下去,在他们(她们)的渴望与鼓励下我终于写完全书。 由此,在形象处理上我采用了“形变”的手法,让书中人自己凸显或凹隐,我不给他们模子(虽说我心里有个底子),我只给他们料子(元素)。一旦在写,他们就已不属于我了。 在整个创作系统中,书中人占第一位,他们控制全局,写作行为占第二位,作者退居最末。我们从本书的性描写、暴力描写与玄言描写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书中人是如何通过其自动化表演把作者逼出本书世界的。 本书很大一部分在正面描写战争,属暴力描写。它是“武”,而不是“武侠”。“武侠”就是“武狭”,它是十分狭隘的东西,所谓“侠之大者”仍然是“侠”,而我在此言的是“武道”(它属于“文道”的范畴)。本书无疑是一部道家之作,全书(包括还未完成的第二、三、四卷)通过对整个东晋朝的人文、政治、军事作全景式的描写,来揭示中国文道在那一段历史时期的存在状况。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文道使然。 我为什么要革新中国历史小说?文道使然。 我为什么要做作家?文道使然。 文道先我而生,我因文道而活。在我幼时,文学对我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长大后我便自觉地献身于文道。“作家”一词对我来说,永远是神圣的字眼。 性情化写作使我坚定,精细化写作使我成功。 我用最原始却最有效的方法改稿:写完后把原稿从头到尾完整地抄一遍,在抄的过程中自然会大改。然后一遍遍地梳理。有心人不妨一试,笨功夫历来最有效。这一点也是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方法吧,我与先生文心同也。 2001年11月1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