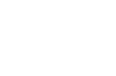江南书全文免费阅读_江南书最新章节
|
【序一】 正是江南好风景 孙昌建 今天是2017年5月4日,已到春夏之交时节,下午的窗外似雨非雨,正是读国文诗歌的好时光。我想我这样的开头,不仅仅是交代一个写作时间,更在于要指向一个历史的节点,即中国新诗一百年的节点,由此来看国文的诗,可能会更有意思。
感谢互联网,今天读诗,准确地说读朋友的诗已变得十分容易和亲切。国文博杂而宽厚,对己甚为严苛,但对朋友的诗文,他一直是以赞美和鼓励为主的,尤其是在形成文字之后。国文愿意尝试多种风格,他的诗歌一直在做着把西湖与大海打通的努力。这种努力的心理前提是,他对之前的诗作是有所不满的,更进一步说,他对同时代的不少诗人的诗作也是并不满意的,我想这应该是诗人写作的另一出发点,所以国文试图改变此种境况,从我阅读的感觉来说,大约是从去年开始,我越来越觉得国文的诗很像台湾诗人的诗。 台湾诗人,如洛夫、痖弦、余光中等,可能因为近期来杭州次数多了,他们也可以公开出席活动并被报道了,不像二三十年前,只能在小范围内品茗、喝酒。我们最早是从流沙河的《台湾诗人十二家》开始对他们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初读惊为天人,因为当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在向民歌学习时,人家早就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欧美现代派,而我们那时的民歌又停留在假大空和顺口溜的水准上,而非真正的风雅颂、真正的赋比兴。然后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批台湾诗人,即使他们是裸奔向西方,也还是黄皮肤、黑眼睛的根底,即不管他们的诗写得多么洋派,也还是中国的当代汉诗,而且跟民国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血脉相连的,跟徐志摩、戴望舒还是一个谱系的。近些年我也听到一些议论,说台湾的中生代诗人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点我也承认,但从社会和文化的现状来看,我以为大陆诗人的处境要更为芜杂,有时还处在一种犬儒的状态中,无非一种是坐稳了犬儒的位子,还有一种没有坐稳,所以暂时以流氓的姿态示人。 读《江南书》,江南扑面而来。这在他的《我是江南王朝的末代废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是江南王朝的末代废主 我只做了三天君王—— 第一天 千里莺啼 第二天 水光潋滟 第三天 暗香浮动 第四天 大雪纷飞 我向虚无拱手让出我的江山 我遣散百花妃子 让她们回到水湄回到山坡 回到美和春天 回到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中去 只带着芍药:我忠贞的王后 开始在宋词中的逃亡 我是江南王朝的末代废主 我不期望分封 更无意复国 我将西湖瘦西湖斫成琵琶 将秦淮河斫成胡琴 将苏堤白堤杨公堤三根琴弦 装在这三把乐器上 我只愿做一个永远的废主 怀抱三把独弦琴 任内心的黑暗 在江南五千年的颓废和孤独中 长出一身闪光的木耳 还有诸如《若惦念,请来旧时光里寻我》《让我离开自己一会儿》等无不都是这样一种趋势,仅从诗题上也可看出这样的情调。这显然是压抑的效果,这种压抑,就是不再高八度,他不是写开花,而是写落花,是落花飘在流水之上,是落花死在了泥泞之中,他是用低音来吟唱这样的意境,因此格外迷人和别致,或许也还有一点点颓废之美。这样的写作,已经为国文在朋友圈里获得了“江南废主”的名声,虽是戏谑,却也是在语言上的一次冒险。对这一批诗,我愿意用标题把它们列出来,这是我在这本诗集中较为喜欢的—— 秋天记 我在江南坐牢 我可不可以这样倒退着看雪 在一面青铜镜里辨认故乡 卷珠帘 有些废墟是我们一生无法抵达的高度 没有谁曾把西湖比作砚台 清明 一声细小的鸟鸣也可以切开天空 我们每天都在一点一点死去 唯有故乡喊我,我才会将整个灵魂转过去 …… 我觉得这样分行的排法,且不加书名号,可能更具美感,这就让我们知道《江南书》是一部怎样的书了。 国文在诗观中说到了写作这一批诗的体会,他说:“在时光的侵蚀下,我们明显地‘旧’了。然而,对此我却没有丝毫的沮丧或悲观;相反,我却越来越迷恋这种‘旧’的气息。岁月褪去了我们身上曾经的鲜亮,生命还复一种璞真,如同某次我在青岛一蛇馆看见的剔去了皮肉的蛇的骨殖,它盘旋在标本架上,洁白、细腻、精致、美丽,宛如一首生命之歌。”是的,这是生命之诗,但这生命却是旧的是老的是前世的,尤如他虚构的“江南废主”,或者就是暗指那个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在另一首诗中他也写到了这位诗人)。 这就让我感觉国文的气质仍是浪漫主义的,或者说他的全部家当是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或者叫新古典吧。这是他的命中劫数,无关褒贬,已成基因,放在全中国来看,国文这样的诗人或许尚能数出几个来,但放在浙江,那只有一个他了。他的这种风格可以近作《吼夜》为例,且看—— 行至路尽头。他像一头濒临绝境的老狼 运足丹田之气 对着前方布袋似的夜空怒吼 他的怒吼声,令夜色颤了几颤 他将一条火龙从喉管里吐出 从窨井里吼出清风 从淤泥里吼出莲花 从峭壁中吼出裂缝 他从绵羊的头颅上吼出犄角 从豆腐中吼出刀子 从酒盅里吼出侠骨 从血脉中吼出子孙 他从自己的身体里,吼出一支黄巾军 诗有好多种,有的诗我们看下来,找不出一个标点符号的毛病,但我不感动;有的诗我觉得很有感觉,但还是发现有一根小小的刺,刺进了诗歌的肉里面,把这根刺拔将出来,是我的一厢情愿,但也有可能久而久之,这根刺风化成了一颗美人痣,成了某种标志之一,这样就得从历史的语境中去看了,正如徐志摩诗中的“沙扬娜拉”。也有可能,是根本没有这根刺,是我的眼睛花了。 我这样说,是我以为好诗也只有在批评和讨论中才能更上一层楼,正如我对“江南废主”的最后一句“长出一身闪光的木耳”中的“木耳”百思不得其解一样,我知其形象,但不知为什么要用这个形象。还有,我对这一首中的“他从自己的身体里,吼出一支黄巾军”中的“黄巾军”也觉得可以拿出来讨论。如果光从意象上看。这是不错的,至少有颜色,且是中国色,也喻意为“造反”或“造反派”,也会让人想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陈胜、吴广等老前辈们。 先不谈“木耳”和“黄巾军”这个意象的所指,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硬盘和软盘。我想讲的是这样的诗这样的写法,实际上是把自己逼到了悬崖绝境。我认为“木耳”和“黄巾军”是两根小刺,尤其是后者,实在是一种观念上的问题。这不是国文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这是历史已经把这些词给污化了,而且我以为在诗歌中做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是颇为危险的。在这本诗集中,以人物为题的一些诗,除了几位古代诗人之外,我以为相对来说就草率了一点。 既然讲到历史这个词,我以为这倒是解读国文诗歌的一把钥匙,至少是一个撬点。比如《口红》一首,一上来就是“一支西周的口红,打败了烽火台”,这作为诗句的确动人,但作为一种历史观或女人观,实在乏善可陈,我倒更期待邻居女子用一支口红能打败诗人的领带……我知道这不是在一个语境上述说,但我们读国文的诗,的确是要去找到他那个历史的撬点,在这个撬点上,撬起了诗人的才气横溢、语词华丽、节奏明快、收放自如,这些无一不在显示着国文的成熟和造诣,同时他的诗又适合朗诵,特别是适合他自己来朗诵。 另外我要说的一点是,国文的“非诗歌”却能把非诗写得非常像诗,这意味着国文的努力和自觉已经开花结果。建构和解构都是构,木构钢构也是构,这就涉及创新和怀旧的统一,暧昧和准确的同步,丰富和抽象的合一,更在于会不会有一颗意想不到的子弹射来。在国文那里,我以为子弹还藏在他身上,他还舍不得掏枪,他喜欢用飞镖,飞镖一出手,江南便落花,这让我想到了杜甫的那句诗,用在今天也可应景,因为今天就是历史中的一天: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的伤感就是国文的伤感,也是我们共同要面对的问题——这就是新诗一百年后的大问题——什么是好诗,什么是一般的诗,什么根本就不是诗?国文以一本《江南书》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而我通过阅读国文的诗来表明我的一些观点,其中见仁见智或见谬都在所难免,因为不管怎样,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样的诗句摆在那里,而且已经摆了一千多年了,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2017年5月4日于杭州体育场路218号) 孙昌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诗创委副主任、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杭州《都市快报》图书工作室主任,出版有诗集《反对》、长篇小说《我为球狂》《我为星狂》《我爱跆拳道》、评论集《我的电影手册》《我的新电影手册》《成长电影》、随笔《浙江一师别传:书生意气》《向来风花雪月》《民国有个绍兴帮》《读白》等二十余部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