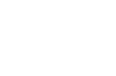父兄被冤杀后,我造反当女帝全文免费阅读_父兄被冤杀后,我造反当女帝最新章节
|
1 父兄蒙冤被诛后,我孤身入朝堂寻天子讨公道。 “臣女裴知月,请旨彻查兵籍,以期父兄案水落石出。” 无数文武大臣炸了锅,指着我怒骂:
“妇人干政,千古未有之先例。” “裴女此举包藏祸心,陛下慎之。” “兵籍重事,岂容私心横行?” 绝望之际,沈砚舟挺身而出,一路为我遮风挡雨。 我手握兵部大权,将昔日诬陷我父兄的政敌纷纷拉下马。 可我知道,我不能停。 太子被废,皇帝病重,临终前将首辅大权交到了我手上。 “新太子年幼,卿可尽力辅佐,若不成器,卿可取而代之。” ............ 我跪在太和殿前,身后是百官肃立,前方是雕金漆柱与身着五爪金龙的天子。 雨很小,几乎听不到声音,只是在我的肩头、袖角一点点渗透寒意,顺着背脊一直往里钻。 我没说一句求情的话,只将那卷我父亲留下的兵籍副本高高举起,语调平稳得近乎冷漠: “臣女裴知月,请旨彻查兵籍,以期父兄案水落石出。” 这话一出口,百官一片哗然。 “妇人干政,千古未有之先例!” “裴女此举包藏祸心,陛下慎之!” “兵籍重事,岂容私心横行?” 我低垂着头,听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轮番落在我身上,像雪落白绫,不重,却足够将一个活人压死。 他们不是不识我是谁。 我是裴家嫡女,是太傅之女,是那年在兵部默诵兵制三章,被说“好女不闻政”的笑柄。 我是那个,在父兄满门遭诛后,还敢踏入朝堂的女子。 ——是个,不识时务的疯子。 可我偏要疯。 我父兄被诛前一夜,将这卷兵籍藏在壁后,留了半句遗言:“若朝廷乱了,你便带着它,去见圣上。” 那日我替兄守灵,蜡烛燃尽,府中鞠绝。 没有人愿意再看我一眼。 除了我自己。 “你可知此举何意?”皇帝终于开口。 我抬起头望着他,眼神不卑不亢:“若我父兄无罪,则臣替他们洗刷冤屈;若我父兄有罪,还请陛下先查实。” “你要的只是调查,不是权力?” “可这朝中,肯替裴家说话的,已经没有人了。”我一字一句,“若不能暂理兵籍,真相只会被人永久掩埋。” 皇帝看了我许久,忽然笑了。 “裴知月,朕记得你,你是当年进宫伴读,状元之女,却宁可不婚、不嫁,进翰苑做外录的那一个。” “你明知不会有未来,还愿意试试。” “那今日,朕便成全你。” 他挥袖一落,群臣色变。 “裴氏暂理兵部兵籍,限期三月。三月之后,若查无所获,若无一策,若无实绩——” “便永世不得入朝堂一步。” 我谢恩时,手掌已经冻得发青,指节僵硬地贴着地面,像是把整个人的命运都贴了上去。 掌兵权,只是表面。真正的意思是 ——我为群臣所不容,他们恨不得我因为调查不力被皇帝治罪,好保全他们一贯的权势。 所以我,必须赢。 兵部衙署比想象中冷清。 我入值的第一日,尚书与侍郎齐齐病假,案前连个正眼看我的人都没有。 我从堂外走入,吏员们低头看账、研墨、拱手送文,动作都极其利落,唯独没人同我说一句话。 像是这里根本不曾迎来新上司,而我,只是个误入的女眷。 “兵部临时命官,裴知月。”我自报家门,语声不大,但所有人都听得见。 没有回应。 我不恼,只拣了案头最靠西角那张废桌,掸了掸灰,坐下。 我知道他们的想法。 一个女子,一个裴家余孽,一个靠哭跪和旧情得来的“兵籍暂权者”。 他们在等我出错。 于是我没有吩咐、没有下令,只安静地等着那份“每日调兵报”递上来。 等了半个时辰,也没来。 我知是故意的,便亲自去库房调档。三番五次,竟真给我找到几份手写兵籍备份——与朝中兵录所记数字对不上。 这一夜我未曾离署。 兵部灯火连夜。 我一页页查着兵籍,对照调兵文书,终于在子时看见一个问题: 一支本应调往东境的兵马,半年未报,但兵饷仍月月核发。 这是——空名吃饷。 有人在贪兵粮。 我用的是太傅旧章。 那枚印章早已被废,但在兵部老吏眼中仍有分量。片刻后,有人悄悄将一份副卷递到我桌上。 他们不是帮我,他们是信太傅。 也够了。 再回神时,已近黄昏。 我望着天边的晚霞,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你这性子,还是这么拧。” 我回头,沈砚舟立在兵部大门外,银冠墨袍,带着监察御史的腰牌,一双眼比多年前更冷了些。 “裴知月,你这是何苦呢?” “你该清楚,陛下给你三月,不是要你立功,而是要你知难而退。” 我没回话,只静静地望着他。 他叹了口气,像是在责备,又像是心疼:“你一介女子,孤身来扛朝堂旧案,你以为你能撑到哪天?你要扛的不是一个案,是整个朝堂的排斥。” 我嗤笑。 “那又如何?我裴家上下百口,难道不配一个真相?” “兵籍在手,不查就是共谋。沈砚舟,你是监察御史,若连你都认命,那这天下谁还能守得住?” 他神情复杂,片刻才低声:“你变了。” 我低头抹去一页墨痕,语气平静: “不,我没变,是这个世道,早就不留给我变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