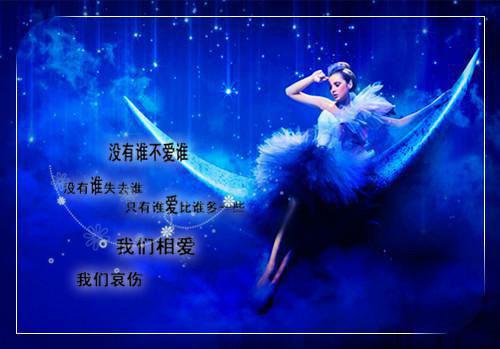重生1991:春潮晚来急全文免费阅读_重生1991:春潮晚来急最新章节
|
挣扎着从罗汉床上坐起来,贺知风头痛欲裂。 睁开眼,看着四周古色古香的摆设,她揉了揉眼睛,觉得有些眼熟。 她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
就在贺知风发愣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剧烈的拍门声。 “知风,快开门!我是你三婶!” 林芳红插着腰,耀武扬威地站在贺家后院,把她的房门拍的咣咣作响。 不远处,十几个长舌妇探头探脑地聚集在院门外,喋喋不休。仿佛这贺家的事,跟她们也有几分关系。 “是贺家那个白眼狼回来了?” “可不是嘛,都离家出走三年了,居然还有脸回来。” “她婶儿真够好心的,居然还给她说亲。” 林芳红听着婶子们的夸赞,脸上的笑容变得愈发灿烂,这语气便稍稍缓和了些。 “知风啊,今天是龚家下聘的日子,你这个准媳妇不露面怎么行?快跟我到前院去,大家可都等着看你呢。” 贺知风不由得晃了晃神,龚家?下聘? 她不可思议地站起来,走到穿衣镜面前,看着镜子里那张柔嫩白皙的脸,呼吸猛然一滞。 “怎么还不出来?唷,还端起架子来了,真当自己是什么大小姐啊!” 等了几分钟,林芳红又不耐烦地催促起来。 “让他们滚!” 贺知风下意识地大声喊道。 林芳红被吓了一跳,身子顿时僵硬了一下。 听到这声,院门口的街坊四邻又像麻雀似的嚷嚷开了。 “以前不是脾气挺好的嘛,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她小时候还美滴很呢,昨天瞧见时,头发却剃的跟劳改犯似的。” “听说她在京市做过那个,搞不好得过什么脏病,只怕头上也长过什么,不剃了怎么办?没法上药呢不是。” 大婶大妈彼此心照不宣,头挨着头低声闷笑,仿佛根本不知道疲倦。 谁能想到,不过出来遛个弯,竟会撞上这么一出好戏。 贺家,那可是他们周县远近闻名的大户啊,居然也出了这等丑事。 “贺知风,我给你三分钟,再不出来我就撞门了!”这下,林芳红是真的有些恼了。 贺知风深吸几口气,彻底清醒了过来。 琥珀色的眼眸骤然笼罩起一层寒气,嘴角却微微勾起。 没想到啊,她竟然重生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此时正是她被二叔贺远征骗回周县不久,遭遇全家逼婚的时候。 而这场荒唐的婚事,正是门外的这个女人,她的三婶林芳红给介绍的。 为了把她嫁出去,林芳红在她母亲俞宛的面前,把龚家吹得天花乱坠,但事实上,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火坑。 上辈子,因为间接造成了哥哥的早逝,贺知风自觉要肩负家族重担,高中一毕业,就在兴懋斋做了雕刻师傅,不管多苦多累,从来毫无怨言。她不求被感恩,不求富贵荣华,只想得到一点最基本的尊重,感受一份家庭的温暖,结果到头来—— 兔死狗烹,弃之如敝履。 当真是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 重活一世,她绝不会再为贺家,断送自己的一生。 “三婶,这婚我不会结的。”贺知风推开门,缓缓地走了出来。 仰起头,雪白的脖颈立即从衣领中露出半截,虽然纤细,却宁折不弯。 林芳红面露惊愕,不知道为什么,今日贺知风瞧着似乎与昨天截然不同了。 她骤然拔高了音调:“日子已经订好了,请柬也都发出去了,你现在跟我说不结?” 贺知风轻挑眉梢,从容不迫地笑了笑。 “堂堂兴懋斋现任掌家,端端架子,你又能奈我何?” 这句话,彻底戳破了林芳红的肺管子,“呸!你一个女娃娃,也敢自称掌家?还是早点嫁人,相夫教子吧。人家龚四海,可是咱们瓷器厂堂堂副厂长,每个月三百多的工资,想嫁给他的黄花大闺女能从这儿排到鼓楼去,要不是看在我和你三叔的面子上,能轮的上你?” 哗啦! 那些婆婆妈妈,又都炸了锅。 “听说,这婚事她妈俞宛也同意的。这么好的对象都瞧不上,莫非她还想回京市去?” “干那行,就那么赚钱啊。” “但这种不干净的女人,龚副厂长怎么可能愿意娶?” “这你就不知道了,她爸虽然死了,但兴懋斋一直都在,等以后分家,能分到不少遗产呢!” 林芳红气得直踹门:“我告诉你,聘礼已经收了,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再不出来,我就......” “就让龚四海找几个混混,趁着夜黑风高把我绑了,送到他家里,一不做二不休,来个生米煮成熟饭?”贺知风不怒反笑。 林芳红心生惊恐,这丫头怎么会知道的? 转眼又更大声地哭嚎:“我滴大哥哎,你劳碌一辈子,为儿为女费心肠哎!不料竹篮打水一场空,生了个白眼狼哎——” “生死贵贱不同命,嫂嫂的苦水吐不尽呐——” 贺知风的眸色愈发阴冷,眸底里早已积满了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