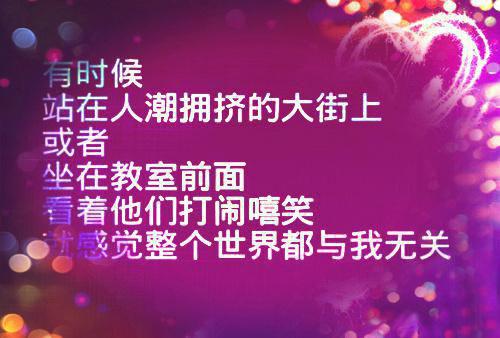前夫给我一巴掌,我去京都当富婆(叶晚棠林远山)全文浏览_前夫给我一巴掌,我去京都当富婆全文浏览
|
一夜未眠,又受了风寒,我很快就病倒了。 我浑身发烫,头晕目眩,时而如坠冰窟,时而似在炭火上炙烤。 林远山见我病得厉害,连忙唤人去请大夫。 偏在这时,柳娇娇又来了。 她就如同深闺中争宠的小妾,每每见我与林远山相处,总要寻个由头将他引走。
这回她又说欣怡摔伤了。 自打她们母女搬来,这已是第八回说欣怡受伤了。 林远山当真是个榆木脑袋,每回不过是些皮肉轻伤,他也信以为真。 若非如此,只怕柳娇娇为了拴住他的心,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要利用。 这一回也不例外,林远山听闻欣怡受伤,便对我道: “你且忍耐片刻,待我送欣怡去看大夫,便来接你。” 我听得一阵心寒:“我都病得起不来身了,你还要我如何忍耐?” 他却道:“你到底是大人,欣怡年纪尚小,受了伤怕是要哭闹的。” 我正欲再说,欣怡却跑了进来。 她一头扑进林远山怀里,哭得梨花带雨,还唤他爹爹。 虽是哭得伤心,但看她活蹦乱跳的模样,分明是无甚大碍。 林远山有些尴尬地道:“欣怡似乎并无大碍,不如我唤辆马车,一道送你们去看大夫。” 我冷声道:“林远山,你是不是该先说说,为何她要唤你爹爹?” 他支吾道:“欣怡无父,见别家孩子都有爹爹,心中羡慕。她唤我一声,我便由着她了,也是怜惜孩子。” 听他这般说,我混沌的头脑突然清醒了几分。 我讥讽道:“她怎会无父?她父亲不正是害得你父母含冤自尽的那个人吗?” 话音未落,林远山抬手便给了我一记耳光。 这一掌打得极重,不知是因我揭了他的伤疤,还是戳破了他的遮掩。 他的心上人嫁给了害死他父母的仇人,如今他还要照料仇人的遗孀***,可笑至极。 但这一巴掌却让我心中豁然开朗,他亲手打碎了我最后的犹疑。 我提笔给姑姑写了封信,约定在下个月就动身去京都投奔她。 虽已下定决心,但我也知道不能全靠姑姑接济。 我得在离开前攒些盘缠。 思来想去,我决定摆个小摊。 这年头,便是想去寻个绣娘的活计也不容易。 那些大户人家的绣坊,都有自己的门路。 所幸如今官府对街边小贩管制不似从前那般严苛。 卖胭脂水粉需要本钱,我手中并无余财。 最后我想到去卖馄饨,我的手艺还算过得去。 开个馄饨摊子也要本钱,我便将林远山成亲时给我的那对金钗当了。 那是他母亲特意留给儿媳的,说是传家之物。 当了婆婆的心意,我心中有愧。 可他们又何曾善待于我? 我让给林袅袅的那份绣坊差事,便是典当了全部嫁妆也换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