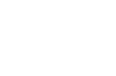弗兰肯斯坦读后感100字
|
《弗兰肯斯坦》是一本由[英] 玛丽·雪莱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弗兰肯斯坦》读后感(一):怪物的悲剧。 一个由各类尸体肌体拼凑而成的一个“怪物”,他身上的任何器官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这个世界也不属于他。弗兰肯斯坦——他的造物主创造了他,满怀期待赋予了他生命,却没有对他负责。世上的人都因为他丑陋怪异的外表而排斥他, 忽略他内心深处的呼唤。他孤身从弗兰肯斯坦的实验室闯入世俗,过着原始的生活,他的心刚开始就像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往里面输入什么。他自己慢慢摸索着怎么填饱肚子,怎么遮风避雨,怎么免受自己收到人类的伤害。他也渴望关爱与平凡的生活,他的内心也曾充满温暖与希望。 《弗兰肯斯坦》读后感(二):书面语有点过 当然这可能是读西方著作的一个公有的东西。 --- 情节没那么复杂,只是由口述出来的人的“啊”,“呀”之类的感慨所渲染,归结起来就是——明明不是戏剧,却非得向戏剧上走去。 --- 作为宗教免疫的人,对立面出现太多的诸如上帝之类的名词,已经诸多宗教相关的概念以及美化,总是有点不适应。 当然这是一部很不错的科幻题材,尤其是考虑到其所处的时代。脑洞得足够大才能想到这样的点子,点子有了,那么必须得拼凑出来足够的字数才能算是完成一部书。 《弗兰肯斯坦》读后感(三):《弗兰肯斯坦》:致与生俱来的罪恶与不屈 ——记录些许看书过程中的零碎观点 一、自然与人类 01·自然孕育人类,其既承担安抚的职责,也承担恐吓的义务。 02·人类,勇敢却无知,道德却自私。 03·感性的冲动,趋势人类无畏的行为,挑衅全知的神与自然。但回归起点,这种感性的冲动难道不是神与自然点亮的吗? 04·基督教的罪赎概念,乃至于奉神视角下对自然和造物主的认知,在这本书中又近乎直白的抒发和呼应。 二、怪物的意志 01·任何一种富有情感的生灵,在其被创造之初,就会陷入一种无从消解的孤独。唯有密切的联结和同类的依偎方可“掩饰”这种孤独,而无论是神还是人,都将这种联结的可能述诸爱情与家庭。 怪物摧毁弗兰肯斯坦的方式,是毁灭他的联结,是迫使他回到孤独之中。而在弗兰肯斯坦的孤独中,同享孤独的怪物,则感受到了一种名为报复,实为共生的联结,从而消解自己的孤独。 02·弗兰肯斯坦是高尚的吗?所有人都在称赞他的道德,甚至怪物都在为他的“残忍”而称颂他的道德。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道德的彰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弗兰肯斯坦对“自我”的维护中,即维护自己的天赋,维护自己的亲属(孤独),维护自己的群体(人类)。 怪物是具有品德的吗?事实上,他是具有的,他渴求知识、渴望爱与美德。但他也确实在无数次被人类社会所抛弃之后,因复仇之火的燃烧,而犯下确实的罪行。如果回归到这本书创作的背景,我们不难在这现实中寻找到这一“失德”过程的呼应。 03·怪物因被创造而天然背负罪恶。他的罪恶不是来源于丑陋,而是来源于“异己”。即使他学会一切人类的行为、语言甚至美德,但是他已然无法根除外貌的丑陋。 如果跳出这本书本身,回到某些书评家对“反叛”背景的认知,我们也可以残忍地将这个行为理解为,“非主流”(异“己”)阶层的人民,纵使其付出何种努力,也难以根除与生俱来的“阶层的丑陋”。 因为,无论是怪物的外貌,还是社会上“异己”者们的阶层,都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但讽刺的是,怪物的外貌由弗兰肯斯坦赋予,却又受到弗兰肯斯坦的厌恶。而社会的“异己”者们的阶层又是为何而生,又为何遭弃呢? 04·摘抄一段书评家的“反叛”论: “(1790)以辉格党人艾德蒙·伯克”为代表的政客恣意攻击法国大革命,哀叹反动王朝的垮台,将革命党人斥责为食人肉的妖魔鬼怪。为了反击伯克的谬论,著名激进派政论家托马斯·佩恩在《人的权利》一书中尖锐指出,任何不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谋利益的政府都必须被推翻。他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彻底摧毁魔鬼般的贵族阶级。” ——在1790s,罪恶与生俱来,丑陋无法医治,正如阶层无法挪移。 附-摘抄和碎碎念: 01·“我现在回想往事,把那地方称为沉寂荒凉的不毛之地,可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那时它是自由之土,欢乐之地;因为在那儿,不受注意的我可以与我想象中的生灵交流。” 02·“自然科学是支配我一生命运的守护神” 【但也是摧毁了弗兰肯斯坦一生的“神”,可见“神”具有“神性”而非“人性”,其并不以庇佑或摧毁个体的目的而存在,其有其自身的喜怒哀乐和行为模式】 03·“获得知识太危险了;一个认为自己的故乡便是整个世界的人要比一个好高骛远、志大才疏的人不知幸福多少倍。” 【根据母亲的观点来说,眼高手低总比眼低手低好些。可见,对于某种被称之“危险”的行为,其所可能带来的命运走向往往兼具有极高的上限和极低的下限。】 04·“如果你所从事的研究有可能使你冷落别人,使你丧失生活的情趣,不想体验那种纯真质朴的生活乐趣,那么,你的研究就是不正当的,换句话说,你就不应该在这种研究上耗费心思。” 【我也不知道弗兰肯斯坦是从自己的命运中要告诫我们“理论终究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还是在发出“不要走火入魔”的呼号。】 附-关于这本书无关紧要的一些事: 家中书架上一直摆着一本《弗兰肯斯坦》,是初中好友送的礼物。彼时聪明又有脾气的他极其顺手地把这本书丢给了我,而不聪明却又脾气的我一面将这本书摆上了书架却不肯“迫不及待”地翻开。后来,和这位朋友争吵数次,最终疲惫不堪地分道扬镳,每回看到这本书便心烦,就也始终不肯翻开了。(但关于我为何仍将这本书一直留在书架上的原因我已经忘记了,或许是因为某种生活的惯性。) 今天课上,舍友老王从图书馆而来,恰巧带着一本破破烂烂的小册子——《弗兰肯斯坦》。据老王表述,她只看了这本书的结局,便决定把这本书带回来看看。恰巧今天不想听课,所以我讨了这本书过来,一鼓作气看完了。 它的结尾确实很吸引人: "我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他大声说道,那激动的神情显得悲怆而庄重。“我此刻的一切感受将化为乌有,锥心的痛苦将一去不返,我将以豪迈的气概登上那火葬柴堆,在熊熊烈焰的烧痛中以苦为乐,心欢情悦。灼灼的火光将渐渐熄灭,我的灰烬将随风飘入大海;我的灵魂将得以安宁,即便它仍能思考,它也绝不会再像这样思考。永别了。” 说完,他纵身跃出舷窗,跳到紧靠船边的冰筏上。转眼工夫,他便被海浪卷走,消失在远方茫茫的黑夜中。 《弗兰肯斯坦》读后感(四):被诅咒的普罗米修斯 身处水泥森林的我们,每日心甘情愿地面对着无数黑色的镜子,任由它们的电流刺入我们的神经。在一番精神麻醉后,又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它们,在空虚与亢奋之间来回摇摆,直至被异化为这些“黑镜”中的符号,如此循环往复,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又避之不及的一部分。 尽管这一切听上去荒诞滑稽,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荒诞就是现实。 像无数科幻作品中所设定的那样,如今的我们恰恰身处这个怪诞而又合理的世界中。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场景与对未来的设想,都可以作为科幻小说的素材与灵感。而早在200多年前,浪漫主义风靡欧洲大陆之时,便有了“科幻”的萌芽,并诞生了一部被后人誉为科幻小说鼻祖的作品——《弗兰肯斯坦》。 比起《弗兰肯斯坦》,我们似乎更熟悉另一个译名——《科学怪人》。然而在这部作品中,并没有十分硬核的科幻内容,甚至关于科幻的细节描述也不多。与其说是科幻,不如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一部“哲幻”小说:一个年轻有为,醉心于生物和炼金术的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带着创造生命的强烈渴求,往返于墓地与屠宰场,用近乎偏执的理性创造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怪物。然而他又因怪物的丑陋而感到害怕,精神因此遭受折磨。随后,他的亲人们被怪物接连害死,而他本人也在对怪物复仇的途中死去。 1.为理性“献身”的弗兰肯斯坦 这部诞生于十九世纪初的另类科幻作品,带着浓重的哥特风描绘了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与怪物之间的博弈。故事中的弗兰肯斯坦出于求知与好奇,以一种相当偏执的理性创造了一个被他认为是“怪物”的生命体,可这种理性却未能在怪物诞生后得到延续,取而代之的则是厌恶与恐惧。 在浪漫主义兴起之时,欧洲诸国依然存留着启蒙思想的余温。弗兰肯斯坦的“理性精神”也正是对时代的部分映射。颇为矛盾的是,弗兰肯斯坦追求理性、追求科学的狂热行为恰恰是非理性的。事实上,令他感兴趣不是科学,而是古老的炼金术,他妄图从中掌握创造生命的奥秘。换言之,他以极端的理性方式演绎了一出非理性的闹剧,想要证明那些所谓的古代科学或异端学说是正确的。然而,怪物的诞生非但没有使他欣喜,反而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作为创造生命的“上帝”,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甚至无法再回到现实生活。 “一个性格完善的人应该永远保持平静坦然的心理,决不能因一时的冲动或突发的欲念而扰乱了自己内心的安宁。我想,即便是探求知识这种事也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如果你所从事的研究有可能使你冷落别人,使你丧失生活的情趣,不想体验那种纯真质朴的生活乐趣,那么,你的研究就是不正当的,换句话说,你就不应该在这种研究上耗费心思。” 尽管弗兰肯斯坦十分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并以此开导自己,但这依然没能阻止他。整个故事中,弗兰肯斯坦的家人朋友始终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而弗兰肯斯坦却没能适时地回应这些关怀,以至于他总是在愧疚中辗转反侧,进而扰乱了他的理智。这大概也是作者玛丽·雪莱对启蒙主义的质疑。理性的追求最终却被理性反噬,于是在失去理智的“理性”中诞生了怪胎。 2.人性与神性的博弈 无论弗兰肯斯坦还是怪物,在他们情绪低落时,总是能在自然风景中得到些许的慰藉,短暂地净化他们的心灵,并试图回归生活,热爱人类,而后者尤甚。当怪物躲进农庄,用至真至纯的心学习人类世界的一切,并以为这份纯真终于可以得到回应时,他丑陋的面容让一切前功尽弃,人间的一切美好从此化为仇恨与妒忌的种子。怪物性情的转变也与弗兰肯斯坦的梦魇相呼应,他所恐惧的不仅仅是怪物,还在于他自己是创造怪物的“上帝”。只因“上帝”皱了眉,于是怪物便不配拥有“人”的资格。 弗兰肯斯坦的偏执、怪物的单纯,如钟摆一般在故事中来回摇摆。一个是神圣的“造物主”,一个是未谙世事的“婴孩”,彼此身上都有神性的影子,却在误解、仇恨中相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弗兰肯斯坦在创造中忘记了现实世界,怪物则在被误解中放弃了对人类仅存的善良。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的故事架构多少借鉴了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弗兰肯斯坦正是像上帝一样创造了“亚当”,然而他自己却在恐惧中化身成为“撒旦”,原本幸福的生活也因此成为了“失乐园”。而这本书的副标题——“现代普罗米修斯”,也正印合了这一形象。唯一不同的是,小说中的这位“普罗米修斯”似乎并不像神话般那样崇高。作为这部作品名义上的主角,弗兰肯斯坦的“盗火”行为是自私的。他的讲述似乎很难让人共情,反而是被赋予生命的怪物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然而,当丑陋成为原罪,美便失去了存在的可能。 3.消失的女性:玛丽·雪莱的生命挽歌 这部小说之所以在后世有如此深远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新颖的题材,更在于作者玛丽·雪莱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女性作家。作为著名诗人珀西·雪莱的妻子,她的才华被丈夫的无限风光所掩藏。今年恰好是玛丽·雪莱逝世170周年,当我们以现代社会的经验与视角重新阅读这部小说时,似乎更能够理解雪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境况。 《弗兰肯斯坦》中虽然不乏女性的身影,但大都是以男性附属的身份出现。甚至被当成一份“礼物”,弗兰肯斯坦的妻子伊丽莎白在故事中初次登场时,便是以戏谑的口吻: “母亲开玩笑地说道:‘我给我的维克托带来了一份漂亮的礼物,明天他就可以拥有这份礼物了。’第二天,她把答应给我的礼物——伊丽莎白带到我的面前。这时,我以一种孩子的认真态度从字面上去理解母亲的话,真的把伊丽莎白当成了我的人——将由我保护,由我热爱和珍惜的人。我把人们对她的赞美,无一例外地看成是对我个人一件私有之物的颂扬。” 如果说,妻子伊丽莎白是作为一份“礼物”而被保护的话,那么女仆贾斯汀则成了主人公弗兰肯斯坦自私的牺牲品。他出于胆怯的心理并未为她出庭作证,反倒是伊丽莎白勇于在法官面前慷慨陈词。令弗兰肯斯坦所胆怯的,正是他所创造的怪物,他担心罪名会加诸在自己身上。而故事中的女性却要在被珍视的状态下不断地遭受摧残,成为一件玩物。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怪物诞生后的遭遇也与玛丽·雪莱自身的成长相关。虽然她生在一个相对优渥的家庭,父母皆为当时的社会名流,但她的成长却并不是开放与包容的,反而受到父亲的许多限制。加之她经历过丧子之痛后,让她开始思考创造生命的意义。故事中的怪物虽然由“上帝”创造,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母亲”,甚至当怪物向弗兰肯斯坦提出为他造一个配偶时,也被对方当面毁掉业已成形的躯体。他担心这对怪物一旦繁衍后,有可能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于是带着对怪物的恶意毁掉了成品,也从此剥夺了怪物对世界的善意。 尽管这些描述在当下的语境中很不“女权”,然而雪莱却清晰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境况与自身的感受。如果生命可以依靠科技手段创造,那么作为母亲的女性又将如何定义?故事中的怪物一次又一次渴求接纳,换来的却是无尽的鄙夷与敌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面前,如此“异类”的存在是否合理,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与夫妻组建的家庭社会结构是否会因此而改变呢? 科幻作品带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奇特的想象力,还在于对我们所处世界的深度反思。正因如此,这部跨越200年的作品至今依然可以成为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照出所有无处遁形的暗影。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https://mp.weixin.qq.com/s/5q7yQ3iwloV5t6lIRkHg3Q 《弗兰肯斯坦》读后感(五):从一处值得商榷的翻译问题谈起——《弗兰肯斯坦》两版序言的文本细读 值得一提,《弗兰肯斯坦》可以是很多东西,但肯定不是第一部科幻小说,类似造人主题的霍夫曼之《沙人》就比它的出现早很多。 玛丽·雪莱写就《弗兰肯斯坦》的动机是什么? 一个比较流行的版本大概是这样的—— 这种剔除了棱角的道听途说经过多方转手,在描摹大体轮廓的同时,既割裂了人物情感,也模糊了故事细节,看起来十分不可靠,我们还是应该从原作者的口述或是手记中,来探索最接近真实的答案,比较可靠的材料是《弗兰肯斯坦》在1817年和1831年两个版本中的序。 这里有必要先提一下《弗兰肯斯坦》的出版经历作为补充—— 那么也就是说本文主要研究的1817年的序是雪莱写就的(事实上,这证据正是出自1831年的序中有言“As far as I can recollect, it(the preface) was entirely written by him.”),而1831年的序才出自玛丽·雪莱之手。值得一提的是1817年的序这样结尾:(采用的是知名度最高的刘新民先生的译本) 然而有趣的是,将这一段翻译与原文对比,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 最明显的便是第二行“and in society which cannot cease to be regretted.”被翻译作“而且当时陪伴我的几位友人亦令我时时惦念,永生难忘”,它在意译上显然有夸张的成分,“时时惦念,永生难忘”则更是过度翻译的体现,刘新民先生或许也是注意到1817年这版序言的特殊性,所以才用过度阐释的方式疏通文意,事实上,我们在文本的蛛丝马迹中时常可以看到不少这样代言的痕迹,比如“a tale from the pen of one of whom would be far more acceptable to the public than any thing I can ever hope to produce”,这里two other friends说的是拜伦和雪莱,括号中补充的部分其实可以更简洁,例如(a tale from whom would be far more acceptable to the public than mine),“the pen of one of whom”从语体简洁的要求来看完全是多余的,除非是在有意强调冗余部分的重要性,从上下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玩一个模仿游戏“a playful desire of imitation”,而胜负双方在结局昭然若揭“The following tale is the only one which has been completed”,但是雪莱似乎对这种结局不是很服气,特地强调了输掉比赛(lost all memory of their ghostly visions)的同时也获得了自然丰厚的慰藉与奖赏,至于他二人那尚未写出的故事其实或许并不重要,因为在当时男性话语权力占绝对主导的条件下,(“the pen of one of whom”)男性的声音远远比玛丽·雪莱“I”代表的女性所能企及的程度更受欢迎,这有点像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言归正传,如果说雪莱为玛丽安排好了身份和地位,那么刘新民的翻译也在设计玛丽的情感,她被标定为“时时惦念,永生难忘”,雪莱和译者在压制改写女性的声音和形象上达成了某种合谋。事实上,仔细揣摩文本语络,这里的“and in society which cannot cease to be regretted.”可能是雪莱想要传达他(和拜伦)对于未能写完故事而输掉比赛长久以来的遗憾。从上文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篇雪莱代言的序充满了男性凝视的声音与想象,作者玛丽被匿名被噤声被代言,而开头提到广为流传的故事也正是截取选材于雪莱一厢情愿的叙述,作为对于男性权力隐秘的一种背书,玛丽的声音和情感,记忆和形象被抹去了,而要将“她”重新找回需要追溯到1831年她亲自写的那版序。 这版1831年的序有待更多文本细读的发掘,它提供了很多之前被遮蔽的信息,玛丽·雪莱清楚而完整地交代了这个故事的有关来源,回忆了童年时独特的写作经历,补充了日内瓦郊外之行并不令人愉快的一些细节,我们惊奇地发现那间日内瓦的郊外小屋中还有之前未曾提及的第四个人(拜伦的私人医生波利多里)—— 在玛丽·雪莱的自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童年的写作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风格。 “It is not singular that, as the daughter of two persons of distinguished literary celebrity, I should very early in life have thought of writing.”玛丽·雪莱的父亲威廉·葛德文是政治家与哲学家,母亲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则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女权辩护》一书的作者,她的家里常有各领域的学术界人士出入,这样的学术氛围与书香家第使得她很早就萌发了写作的念头,作为非常喜欢的消遣,在谈及自身写作习惯时,她自称为“a close imitator”,解释道“rather doing as others had done, than putting down the suggestions of my own mind”,“doing others had done”,这种改写者(或说是组织者)的写作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后来的创作理念,她在序的后半部分用了大量的典故和笔墨来为这种溯源的写法寻求合理性—— “out of chaos”或许暗示了玛丽对于他者材料的广泛取用,哥伦布与鸡蛋的故事则又将这种改写提升到形而上的层次,它的奥秘在于把握事物潜在的作用,并使得其中蕴含的设想塑造成形。 日内瓦之行对于玛丽而言,或许是并不愉快的,在十四年后她依然能对那段经历中令人不快的细节记忆犹新,正如先哲所言,“写回忆录的唯一秘诀便是活得足够长寿”,1831年,拜伦已在希腊遇雨受寒去世七年了,与雪莱在斯贝齐亚海上覆舟相隔也有九年之长,时间抚平一切难言之隐,而让遗憾与心结开口说话,玛丽·雪莱坦白的心迹应该是足够可信的。 我们可以想象自己作为一个饱受女性主义思想熏陶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子,在日内瓦连绵阴雨的家中听着或许不那么令人舒服的鬼故事,那其中包含了大量男权色彩的自我颂歌,与对女性的厌恶敌视,而在每日的上午又因自己作为女子尚未写出故事而遭到反复令人尴尬的诘问,在渴望自我证明的焦虑中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却一无所获。 如果这依然无法通向理解的共情,我们可以诉诸于揣摩原文中微妙的语气—— 若是说这些男性气质的凝视与大男子主义的幻想接近一种侮辱与嘲弄,或许会言过其实,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小屋中发生的是一场关于文字与才情的博弈游戏,胜者可以趾高气扬地沾沾自喜,宣称对于他人的胜利,并且以此来获得优越的凭借与调侃的谈资,进而排解困居家中的无聊,我们唯一的女士在一开始是被当作确凿无疑的失败者对待,更是在性别的双重歧视(鬼故事与现实境遇)下加深了刻板偏见;这种和女士的相处方式对于英国绅士而言显然是粗鲁无礼而令人不适的,何况是对于一个出生于书香世家有着长期写作爱好的女性作者而言,这种对于才疏笔拙与创作无能的嘲讽简直是最大的侮辱,《弗兰肯斯坦》既是一种自我证明,也是最为有力的回击。 因此再来细读开头致萨维尔夫人的几封信中,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为什么温文尔雅、谦恭随和的美好品质都是属于孤独者的,为什么要那么多次强调知己难寻的孤苦无依,为什么美好的品德往往属于女性温柔的哺育,而男人的形象则更多是粗鲁野蛮、暴躁易怒的,为什么疯狂渴求荣誉的副手被描述为“其偏见并未因他所受的教养而淡化”……玛丽·雪莱或许想借此回击三位男士的粗鲁无礼,作为女性声音与立场的内在抗争。 (3)“改写”是男性声音的附庸吗? 若是仔细地研读1831年玛丽·雪莱的序,就会发现她往往会过分强调男性对其施加的影响,而屡次将自己视作那种影响的附庸与产物,来为自己的作者身份寻求合法性,文本的缝隙之中时常可见男权社会的倾轧与胁迫—— 例如她自述作为女性创作者并没有将自己写成故事里的主人公,因为平淡无奇的生活实在无法想象那些富有浪漫色彩的悲欢离合的发生;例如雪莱对玛丽创作的焦急与催促是为了不辜负她父母的声誉,但主要应该是父亲的声誉,因为1817年雪莱代写的序言中明确表述了是献给玛丽的父亲的;例如文中多次承认拜伦与雪莱杰出的才情使得玛丽得到感化,对她的创作有很大的助益,但是他们在小说写作上全然缺乏天赋,不太善于构思故事与人物情节,却也必须反复强调他们的鼓励与帮助…… 事实上,1831年序中多次提及男性声音对其施加的影响,正与《弗兰肯斯坦》的出版经历密不可分,这尤其体现在序言的开头与结尾—— 与其说时人不愿相信这样年轻的小女孩会想出这样可怕的故事,不如说他们不愿意承认女性能如此详尽地构思出这样一部杰作,正如日内瓦的三位同伴那样每日上午诘问道“Have you thought of a story?”他们是同一伙人,都不愿意相信女性的想象力能写出一个精彩吓人的鬼故事,《弗兰肯斯坦》最初的匿名发表估计也是出于风化教养之类原因对于女性的压制。玛丽也在序中回应了这些无礼的读者—— 换句话说,这意思也接近于“leave me alone.Shut up your filthy mouth.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因此,我以为玛丽在序中为自己的改写创作寻找依托的母本,这种写作习惯或源自中世纪缮写者的谦逊,并不应当全然视作对于男性声音的依附,而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反击,这些女性改写者会选择一些迂回的方式,相对不会被社会所批驳的立场来写作自己的东西,通过伪装在合法范畴的边界上小心翼翼地游戏,来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反而具有一些女性化的气质,弗兰肯斯坦造怪物那部分就像是一个剥离了子宫的母亲。 《弗兰肯斯坦》读后感(六):鬼故事的诞生——趣谈悬垂于《弗兰肯斯坦》的几条鬼影 一八一六年的夏天,日内瓦郊外的气候相当反常,连绵阴雨将四位年轻人困在拜伦勋爵租住的乡间别墅间,雨水如注,气氛沉闷,直到傍晚时分,他们便围坐在熊熊燃烧的壁炉旁,阅读几本翻译成法语的德国鬼故事来自娱自乐,其中一位跛脚的男士提议道“不如每个人都来写个鬼故事吧”,但后来只有一位女士的故事得以完稿,于是就有了《弗兰肯斯坦》。这类常见于故事会的传闻还是更适合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它概述自珀西·雪莱为1917年匿名出版的《弗兰肯斯坦》所作的序,故事到这里其实并没有完结(第一段结尾的那个句号看起来虚伪至极,如果它是省略号的话,还或许值得原谅),相反在这之后故事才刚刚开始,只要它还在被人传述,被人铭记,那么它就永远在自我生长,自我偏离。 上面这段话跟所有其他的概括一样含糊其辞得令人讨厌,我们完全可以提问——那几本翻译成法语的德国鬼故事到底讲了什么?另外三个人分别讲了什么鬼故事?真的只有玛丽·雪莱的故事完稿了吗?《弗兰肯斯坦》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那个环境和其他故事的影响?…… 还是让我们忘了那个不靠谱的概述吧,它只是通过有选择的遮蔽和取舍使得本就复杂的现实更加扑朔迷离,玛丽·雪莱应该也是对这种说法颇有不满,在她1831年为《弗兰肯斯坦》第一卷“通俗版”写就的序中,她一一回答了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问题,我决定在每个小节的开头直接摘引相关原文片段,来尽量省去无聊多余的介绍和百无一是的翻译。 据玛丽·雪莱在十四年后所记,她还能记忆犹新而恍如昨日所见的是上文提及的两个带着浓重哥特色彩的故事,其中一本名为“the History of the Inconstant Lover”,书中的那个男人曾向自己的新娘发誓不变心,但当他拥抱她时,发现自己搂着的却是一个面色惨白的女鬼,原来他怀中的女子正是曾经被他遗弃的,此刻恰巧变成了女鬼,类似的桥段似乎在哥特风格的艺术作品中较为常见,蒂姆·波顿2005年拍摄的动画片《Corpse Bride》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节,碰巧的是男主人公也叫作维克托。 还有一本讲的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家族缔造者,他的命运十分可悲——他的家族已注定灭亡,他不得不在几个年幼的儿子长到充满希望的年龄时,将死亡之吻赐予他们。半夜时分,他那巨大的影子出现了。只见他全副武装,除面罩朝上掀开外,活像《哈姆雷特》中的鬼影。在忽明忽暗的月光下,他沿昏暗的大街缓缓走着,最后消失在他宅院围墙下的阴影里;少顷,一扇大门洞开,随即传来脚步声,卧房的门开了。他走到孩子们的床前,见他们蜷着身子,睡得正甜。望着自己青春年少的孩子们,他不禁黯然神伤,脸上流露出无尽的悲哀。他弯下腰亲吻他们的额头,孩子们顿时像被摘下的花朵凋残消亡了。我后来再没看过这些故事,然而我对故事的情节却仍然记忆犹新,仿佛昨天刚刚读过一样。 “Lord Byron ,Percy·Shalley and John Polidori(Byron's physician)” “yes,it’s us.” 根据这段清晰的记录,我们一一来讲述有关三位男士的故事: 珀西·雪莱并不善于构思故事的人物和情节,于是他根据自己童年时的一段经历动笔写了一个故事,他并没有得以完稿,珀西在代写的1817年版的序言也承认了这点。 波利多里想出的故事被玛丽以“terrible”来形容,即使是在十五年后,她还记得他所讲故事的大致内容——一个骷髅头女人透过钥匙孔偷看(偷看的东西她忘记了,但肯定是什么粗俗低级的事情),可是当波利多里将骷髅女人的下场写得比大名鼎鼎的考文垂的汤姆还要凄惨时,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写下去,便不得已将那女人打发到卡普莱特家的墓穴中去了,这是唯一适合她的地方——细细揣摩玛丽的语气,是可以体会出她对于这个故事中包含着的对于女性的恶意较为不满,以至于即使过了十五年之久,旧事重提依旧可以将细节记得那么清楚,这种忿忿体现在对于篇幅和叙述对象的选取上,当她对更为知名的拜伦与雪莱的鬼故事几乎只字不提(尤其是对当时的情人雪莱,几乎以一种挽尊的姿态),却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这样关系较疏的波利多里先生的鬼故事,要么是因为他的鬼故事实在精彩可怕极了,要么是因为玛丽确实感受到很深的冒犯,又或许是两者皆是。 拜伦所讲故事其中的部分情节后来被他附印在他的长诗《Mazeppa》的末尾,取名为《A Fragment》,这个故事是根据拜伦在巴尔干半岛旅行时听到的吸血鬼传说改编的,正如题名所暗示的那样,它并未完成而只是一个残缺的片段,小说以书信的形式写成,叙述者在一封信中讲述了发生的事件,这封信的日期是1816年6月17日。叙述者与老人奥古斯都·达维尔 (Augustus Darvell) 开始了一次东方之旅。在旅途中,叙述者发现达维尔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等他们都到达了土耳其墓地时,老人达维尔在临近死亡之际,与叙述者达成了一项协议,叙述者承诺不向任何人透露他即将到来的死亡。此时出现了有趣的异象,一只鹳出现在墓地,嘴里叼着一条蛇。达维尔死后,叙述者震惊地看到他的脸变黑,他的身体迅速腐烂,小说这样描述道: 于是达维尔被叙述者埋葬在土耳其公墓,而叙述者的反应是坦然的:“我无泪可流。”故事到这里便奇怪地结束了。据波利多里透露,拜伦勋爵打算让他以吸血鬼的身份再次复活,但是他并没有完成这个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拜伦是最早描写吸血鬼的作者之一,有关吸血鬼的第一首诗便是出自拜伦勋爵的《The Giaour》,但这不是本文关心的重点,从略。有趣的是这个故事残片后来启发了在场的听众波利多里,被他改编成为一部完整的小说《The Vampyre》(《吸血鬼》),它是西方浪漫主义吸血鬼文学的先驱。因而这样看来,珀西·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的预言依然是有失偏颇的,《弗兰肯斯坦》并不是唯一得以完稿的故事。 正如这段1831年序开头所显示的那样,玛丽特地写这版序的主要用心之一是提供故事的有关来源,来向屡次质疑的读者回应,她作为一个年轻姑娘是如何将这样可怕的事情描述得如此详尽的,另外玛丽在序中又特别强调了她独特的写作方式——可以称作一种类似改编的写作,她自称为“a close imitator”,所作的无非是“doing as others had done”,这或许并不是出于谦逊的托词与辩护的矫饰,而是一种真诚的写作观念的袒露,因为玛丽·雪莱在序的后半部分又重提了这种文风,将其上升到哲学层面—— 这种近乎老实的写作意识换句话说是有意地溯源,寻找之前发生的事情建立联系,在混乱的多元而非空白的虚无中发明创造,作家的创造性体现在把握事物的潜在作用,并塑造与之有关的联想,玛丽所引的哥伦布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她的观点——西班牙一大臣曾对哥伦布声称,其他人也能发现新大陆,哥伦布便向大臣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将鸡蛋立在桌上,但是无人成功,哥伦布便将鸡蛋一头往桌面上一敲,蛋壳碎裂后鸡蛋便直立起来。 也就是说玛丽这样的作家并不创造新的鸡蛋,而是为鸡蛋寻找新的支撑点,发掘已经存在的故事与意象的潜在可能,并在它们之间建立新的关联。这种守拙的姿态并不是缺乏天赋的体现,而更多是一种对广阔未知与人类探索出于谦恭的真诚。 结合以上这两点,玛丽时隔十五年之久在序中提及的每个故事都应该被高度重视,它们并不是闲情雅致的消遣谈资,而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作家——一个真诚到愿意坦白创作思路并尽可能地提供灵感来源的作家——留给后世的一个小说写作经历的活样本,与其产生鲜明对比的是如今这个极度强调独创性以至于扭曲的时代,一些天资平平的作家却叫嚣着割断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关联,如此推崇自己发明的空前绝后,其实他们不过是将先人早就讲过的故事换了一种并不高明的说法,我更倾向于认为人类的创作是一条代际相承的河流,凭空发明是极少的,更多的创举实质是对于传统的重组与改造,天才能在何种程度上突破这种规则,值得深思。我惊叹于玛丽·雪莱不加掩饰的坦诚。 话说回来,我们不妨来找一找这些立在桌上的鸡蛋吧:玛丽在序中用同样的坦诚交代了小说构思的前后经历,在众人心急如焚的日日催促之下,玛丽先是经过了才思枯竭的焦头烂额,之后偶然在旁听拜伦与雪莱关于生命起源本质的长谈时—— 突如其来的想象力就这样降临了,那一连串鲜明生动的场景攫住了她的脑袋,而这些场景正是小说最初的故事之基,后续篇幅得以增添开拓的起点—— 事实上,这里提及的场景集中出现在全书第五章的开头,我们可以将其视作整本小说构思张开的基点。我们不必提达尔文博士在拜伦与雪莱传说中的电疗法实验对标于玛丽想象图景中邪恶的人体实验,类似的影响关系还有更多的方面可谈,笔者下面扯谎的鬼话都不是定论,而只是暗示一种原型相关的可能性,毕竟现实与思维的关系混沌无章,我们尝试旁加窥探的目光也只能知趣地小心翼翼,我想请读者仔细地回忆笔者在前面逐条考究的小故事,一起来体会这种微妙的影响与悠然的相关性: 若是我们还记得那第一本鬼故事,对,就是新娘突然变成女鬼的那个故事,在读到维克多叙述中在日内瓦与新娘伊丽莎白结婚的晚上,新娘被恶魔勒死成为冰冷的尸体时,在命运弄人的冰冷嘲谑中会不会感到一丝气韵相通呢? 如果你还记得第二本鬼故事中,罪孽深重的家族创建者在亲吻睡梦中孩子的额头,他们便像是被摘下的花朵般凋残消亡了,那么拜伦讲的鬼故事残片中那个尸体迅速腐朽溃烂的老人也一定不会让你陌生。值得一提的是,我以为在第五章中维克托冲出实验室所作的噩梦中梦见他亲吻伊丽莎白时,她的双唇顿时变得如同铅灰,面容也发生了改变,就好像搂着死去的母亲一样,周遭是墓穴与裹尸布的景象,我以为这个故事应该是上述两个鬼故事形象的综合,维克托便是那个罪孽深重者的另一个文化替身。 至于拜伦讲述的吸血鬼故事残片,则为小说贡献了死而复生的情节,这本是拜伦故事中吸血鬼的专长,却被移用到对于怪物的构想上,如果再去读读拜伦勋爵在《Giaour》(1813年出版)中关于吸血鬼的描述,就可以发觉《弗兰肯斯坦》中构思的科学怪物和吸血鬼的特点具有高度亲缘性: 两作在情节上过度相似的暗合几乎难以让人否认玛丽·雪莱在拜伦塑造的吸血鬼形象中获得了小说的巨大启迪。 而话说回来,《弗兰肯斯坦》中的名场面——“He sleeps; but he is awakened; he opens his eyes; behold the horrid thing stands at his bedside, opening his curtains, and looking on him with yellow, watery, but speculative eyes.”——这里应该是受到波利多里所讲那个故事的影响,维克托也因为实验室中的那一瞥而饱受无穷的折磨,那钥匙孔中的偷看转化为凝视的意象,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床帘之前,作为弗兰肯斯坦永恒的困扰。 |